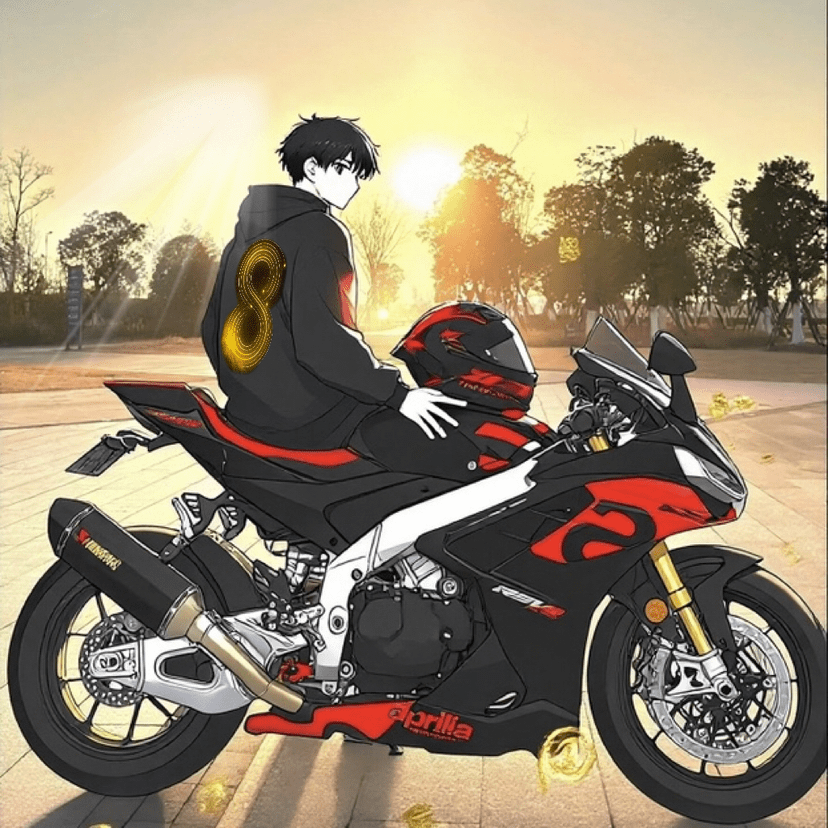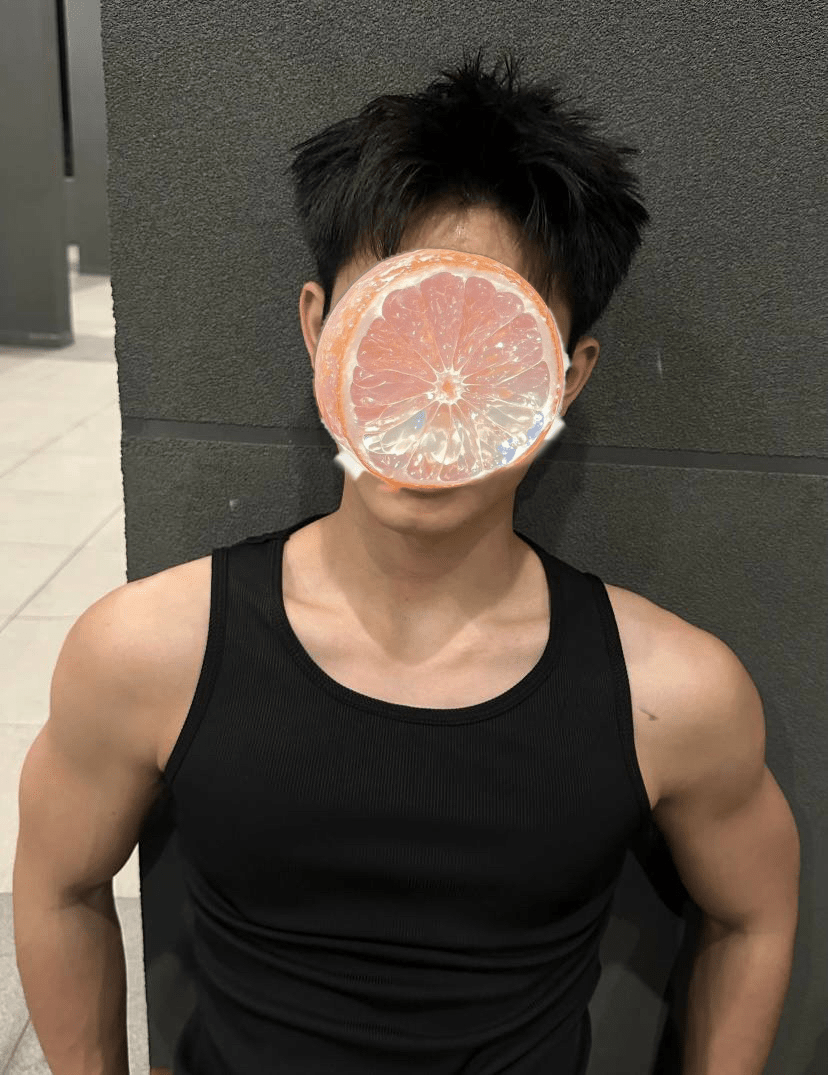本文由 @SafePal 贊助
@万联welinkBTC 創作
我將講訴我的離奇經歷,我在大佬手下的真實故事!
22年我從江西吉安一上市公司副總離職,青年得志,總想大展宏圖,又明白自己不過是一個三無人員,無背景,無人脈,無資金,就經過幾輪介紹,在北京見到一位退役少將。
一開始我也以爲電視裏的騙局,我幾經查證確實真實,然後拜入門下,我以爲我終於觸碰到國內的天花板,故事纔剛剛開始。
開始他們也對我抱有隔閡,問我願不願意加入他們,願意的話可能要拋棄很多,我當時已經忘記了一切,我答應了,我進入到北京順義,一個由監獄改造的學校,國際防衛安全學院,進行全封閉管理訓練,沒收手機,部隊化訓練,有安全防衛,暗殺,搏殺,射擊,我的車技身體都在裏面得到了極大的提高。
還經常會遇到全球各地回來的僱傭兵,其中伊拉克僱傭兵白曉保還教過我健身,我的世界觀,遭遇極大的衝擊,因爲它們跟黑石集團有合作,我一度以爲自己也會走上這條路。
半年後的一天,監獄大門打開,我已經跟社會失去了半年聯繫,後面開始逐步融入他們的組織,執行一些簡單任務。又過了3個月我終於再見到那位大佬,不過我們都喊他老大。
從北京3輛商務奔襲深圳,在南山區一個別墅裏,我開始了我的魔幻經歷。
奔襲到南山區TCL 園區旁的別墅,路口是深圳駐香港的一些部隊大院。
我們一班是 3 個人平常負責生活起居,特殊的情況也要處理一些問題,平常負責生活起居也要照顧大家的日常喫飯,我也是在這個時候練就了一手好廚藝,基本上天南地北的菜都會做,因爲經常要宴請客人。
光喫喝往來已經讓我跌破眼睛,老大不喝酒卻很有很多人送酒飛天茅臺都是幾十件起送,其中不乏 30 年 70 年茅臺,讓我開了眼界的是茅臺居然還有金幣金盃金鑰匙,晚上拿到手機去查價格的時候一瓶就近 70 萬,別墅的負二樓只有我剛到時打掃衛生,搬古董的時候纔去過,一眼望去,全是古董字畫,然後就再也沒下去過。
然而我們 9 個衛士只能住在別墅的頂樓倉儲間,但也比在學院的時候輕鬆很多,也自由些,有時候還能偶爾出去喫一頓自己想喫的,體能訓練也只有每日早晚各一次 3 公里。
就在深圳的幾個月裏我迎來了新年,每日工作大多就是安排日常生活,當司機,出門的時候做安保,短短几個月見到太多太多高官大商。
我也是在這個時候嶄露頭角,因爲我的手藝比較好,很多時候來客人也是我做飯,我也會猜想一下客人,主人的喜好,也是慢慢獲得了一些信任,也去負責了一些更隱祕的工作。
原來這些大佬也有大佬的問題,不過是我託你幫忙,你託我幫忙,有部隊想要升職的,有走私被抓想疏通關係的,有想接部隊工程的,有想爲兒子鋪路的太多太多。
在廣州酒店時,遇到一位現在已經落馬的部隊高官,當時被查很緊張,到處在謀求關係想要脫生,然而我們老大也是手眼通天,原來他也只是一個關卡,上面還有更重要的人。
也是在這個時候我們這一波人要被分開去幾個地方負責各自的工作線,有三個可以挑選去的地方,俄羅斯,緬甸,南京,我一開始想去俄羅斯,因爲可以見識到更大的天地,不過也是真的危險,在我們從新回到北京的時候,我們被安排了一場問話,也就是這場問話,讓我確定了接下來兩年的人生。
那天我們還在北京順義的學院裏,訓練中說是老大要來,我們穿戴整齊在學院門口列隊迎接。
然後就是按順序進行談話,一開始就是問問怎麼樣,有沒有想法,想去哪裏,聊聊天就下一個人,當時我一心想闖出一番天地,談話中我說我想去俄羅斯,不僅能出國而且會安排大學進行學習,雖然遠和辛苦一些,但總是能夠換一番天地,結果並不如我所願。
後續安排是我去了南京六合區,當地一個深圳國資委下屬企業在南京六合區進行項目開發,我也順理成章去任職,項目可查現在已經爛尾,六合區的一個溫泉度假區。
這個時候已經 23 年的春夏時節,那時候地產已經寒冬,老大過去接手注資 3 個億看能不能救活項目,其中牽扯太多,幾方人馬在爭奪國家資產,沒有一個人關心項目到底能不能活。
我也是在這個時候鬼迷心竅,做了超出自己能力範圍的事情,進駐項目後,有錢了大家都很開心,光光在我負責的區域內我都能夠感受到資金在大量被浪費,這也是後來問題爆發的其中之一。
因爲我之前在阿里負責過各類商業運營,當時度假區內還沒有飯店,老大也讓我負責開一家農家樂,一是解決接待喫飯問題,二是工地確實無聊得弄點樂趣,其中牽扯就開始了。
當時我與老大下屬一個公司合資進行承包一些度假區內的零散業務,其中包括農家樂,垂釣園,超市,露天酒吧等等,當時想法很美好,結局很悲慘。
也就是抱着美好的願望我在短短一年內破產了。
項目爛尾的陰霾籠罩着整個六合溫泉度假區,曾經的宏偉藍圖如今只剩一堆鋼筋水泥和無人問津的空地。我站在農家樂的門口,看着遠處工地上一片狼藉,心中的滋味難以言喻。
一年前,我滿懷憧憬來到這裏,以爲能借着老大的資源和自己的能力闖出一片天,卻沒想到,這片土地成了我的滑鐵盧。
農家樂、垂釣園、超市、露天酒吧——這些看似簡單的生意,卻因爲層層利益糾葛和我的天真判斷,變成了吞噬我所有積蓄的無底洞。
合資公司的合夥人表面上對我笑臉相迎,背地裏卻在賬目上動手腳,度假區的管理層對我的“外來戶”身份充滿戒心,工地上的工人因爲拖欠工資時常鬧事,而我夾在中間,成了衆矢之的。
更糟糕的是,老大的3億注資並沒有如預期般救活項目。資金像流水一樣被各種關係戶和中間人瓜分,真正用到項目上的少之又少。
我開始懷疑,老大讓我來南京,根本不是爲了讓我建功立業,而是把我當作一枚棋子,用來平衡各方利益。
在南京六合區的溫泉度假區項目中,我的生活彷彿被按下了快進鍵。表面上,我是老大團隊的一員,負責度假區內農家樂、垂釣園、超市等業務的運營,看似風光無限,實則暗流涌動。
項目的背後,是多方勢力角逐的複雜棋局:深圳國資委、地方官員、地產開發商、甚至一些隱祕的“掮客”,每個人都在爲自己的利益博弈。
而我,一個曾經意氣風發的青年,如今卻在這一場場博弈中逐漸迷失。
23年秋天,事情開始急轉直下。一天晚上,我接到一個匿名電話,對方壓低聲音警告我:“別再查賬了,有些東西不是你能碰的。”
我愣住了,最近我確實在覈查農家樂和超市的賬目,發現不少資金流向不明,合夥人總是以“公關費用”搪塞我。
我本想上報老大,但電話讓我意識到,這背後可能牽扯到比我想象中更大的利益網。與此同時,度假區的工人開始大規模停工,數百人堵在項目部門口,要求兌現拖欠的工資。管理層把責任推到我頭上,稱是我負責的“配套設施”收入不足,導致資金鍊斷裂。我試圖解釋,但沒人聽我的。
工人們的情緒越來越激動,有人甚至砸了農家樂的玻璃。我站在人羣前,試圖安撫,卻被一個憤怒的工人指着鼻子罵:“你個外地人,拿我們的血汗錢去揮霍!”
那一刻,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立。曾經在深圳別墅裏爲高官大商烹飪美食的我,如今卻被一羣憤怒的工人圍困,身後沒有一個人站出來爲我說話。
溫泉度假區項目啓動之初,3億元的注資讓所有人眼紅。表面上,這筆錢是爲了“救活”項目,但實際上,大部分資金被迅速瓜分。施工方虛報工程量,供應商提供劣質材料,管理層中飽私囊,甚至連我負責的農家樂和垂釣園項目,都被要求“配合”某些關聯公司的賬務操作。
我試圖保持底線,但很快發現,拒絕參與意味着被邊緣化,而參與則讓我越陷越深。
與此同時,我與老大的一個親信——一個叫徐峯的副手,產生了直接衝突。徐峯是老大的“老兄弟”,40多歲,精明而強勢,負責項目的財務審批。
他看不上我這個“外來者”,認爲我不過是老大一時興起提拔的小角色。他多次在會議上公開質疑我的運營方案,甚至暗示我的農家樂項目“喫回扣”。我試圖解釋,農家樂的虧損是因爲初期投入過大、客流量不足,但他根本不聽,反而要求我將部分業務外包給他的“關係戶”。
有一次,我在農家樂的賬目中發現一筆異常支出:一筆標明“設備維護”的50萬元款項,實際上流向了一家空殼公司。我追查下去,意外發現這家公司與徐峯的親戚有關。
我將此事私下向老大彙報,希望得到支持,卻沒想到老大的反應出奇冷淡:“小李,有些事你別管,做好你自己的就行。”這句話讓我心頭一涼,我開始意識到,即便是老大,也未必完全信任我。
度假區項目不僅內部矛盾重重,外部的阻力也接踵而至。
六合區的溫泉度假區本是當地政府招商引資的重點項目,但隨着地產寒冬的到來,地方官員的態度開始曖昧。一些官員希望通過項目撈取好處,另一些則對深圳國資委的強勢介入不滿,暗中支持本地開發商製造麻煩。
有一次,農家樂剛開業不久,當地一家“地頭蛇”性質的餐飲公司找到我,聲稱我“搶了他們的生意”,要求我支付一筆“保護費”,否則就讓我的店開不下去。我拒絕了他們的要求,結果第二天,農家樂的食材供應商突然停止供貨,理由是“收到了匿名威脅”。我試圖通過老大的關係疏通,卻發現這些地頭蛇背後竟然也有高層的影子。徐峯甚至冷嘲熱諷:“小李,你不是很能幹嗎?怎麼連這點小事都搞不定?”
在內外夾擊下,我的處境越來越艱難。農家樂、垂釣園等業務的虧損日益嚴重,資金鍊幾近斷裂。我試圖通過優化運營、引入新菜品、舉辦活動來吸引客流,但效果甚微。
更糟糕的是,我發現自己當初與老大下屬公司合資的合同中,隱藏着不平等條款:一旦項目虧損,我個人需要承擔大部分債務,而對方几乎沒有風險。
2023年秋天,項目徹底陷入停滯。3億元的注資早已被揮霍一空,度假區的溫泉酒店主體建築成了爛尾樓,工人們紛紛討薪,供應商上門追債。我的農家樂和垂釣園也因資金鍊斷裂而關門,超市和露天酒吧更是連開業的機會都沒有。
我背上了近200萬元的債務,個人賬戶幾乎被清空,連租住的小公寓都付不起房租。更讓我崩潰的是,老大在這個時候突然“失聯”。我試圖聯繫他,卻被告知他已前往海外“處理事務”。
徐峯則趁機對我落井下石,散佈謠言稱我“私吞上了”項目資金,導致項目失敗。我試圖向學院的負責人求助,卻只得到一句冷冰冰的回覆:“你自己惹的麻煩,自己解決。”
在最絕望的時刻,我收到了一封匿名郵件。郵件裏是一些關於徐峯和地方官員勾結的證據,包括賬目記錄、錄音片段,甚至幾份祕密合同的掃描件。寄件人沒有署名,只留下一句話:“想翻身,就用好這些。”
我猶豫了整整三天。使用這些證據,意味着徹底與徐峯、甚至整個組織翻臉,風險巨大;但如果什麼都不做,我不僅要揹負鉅額債務,還可能被徹底踢出局,甚至面臨更嚴重的後果。我開始暗中調查,聯繫了幾個在學院時的老戰友,試圖拼湊出真相。
同時,我也找到了一位在南京的舊友——一位在媒體行業工作的記者,名叫張然。他告訴我,六合區的項目背後牽涉更大的利益網絡,徐峯只是其中一環,而真正的“大魚”可能指向更高層的某些人物。
2023年冬,我決定孤注一擲。我將證據整理後,匿名交給張然,由他在媒體上曝光。與此同時,我聯繫了深圳國資委的一位老同事,暗示項目資金被挪用的情況。幾天後,徐峯被調查的消息傳出,地方几名官員也因“經濟問題”被帶走詢問。溫泉度假區的項目徹底停擺,但我的債務問題卻因資金追回而得到部分緩解。
然而,這場勝利代價高昂。我徹底失去了老大的信任,組織內部開始對我冷處理。我知道,自己不可能再回到那個圈子。
2024年初,我悄然離開南京,回到江西老家,帶着一身疲憊和少得可憐的存款,開始重新規劃人生。
回到吉安,我開了一家小小的餐館,憑藉在深圳練就的廚藝,生意勉強維持。過去的經歷像一場夢,魔幻而危險。我偶爾會想起在北京順義的訓練場,想起那些僱傭兵的面孔,想起老大別墅裏堆滿的茅臺和古董。但更多時候,我慶幸自己還能站在陽光下,過着普通卻踏實的生活。
現實告訴我,所謂的天花板,從來不是觸手可及的。它背後,是無數交織的利益、背叛和風險。而我,最終選擇了平凡,卻也選擇了自由。
夜深了,小飯館的最後一桌客人醉醺醺地離開,我擦着桌子,目光落在牆角的舊電視上。新聞里正在報道南京六合溫泉度假區的爛尾事件,幾名官員被帶走調查,但語焉不詳。
我心頭一緊,關掉電視,鎖上門,回到後廚的小隔間。那張從南京帶回的U盤,藏在牀板下的暗格裏,裏面是度假區賬目的副本,還有一些我在深圳別墅偷錄的對話片段。
我本以爲逃回江西老家,就能甩掉那段魔幻人生,但老大的影子如影隨形。
半個月前,一個陌生號碼發來短信:“別以爲躲起來就沒事了,老大讓你回北京。”我沒回,換了卡,卻總覺得有人在暗中盯着我。昨天,飯館對面的菸酒店老闆無意提起,最近有個穿西裝的陌生人打聽我的底細。
我點上一支菸,思緒回到南京六合的最後幾個月。那時,我隱約察覺老大不是簡單的退役少將,他的背景像一張巨大的網,籠罩着我,也讓我窒息。
今晚,我決定再聽一遍U盤裏的錄音,也許能找到些線索,弄清楚老大到底是誰,到底想要什麼。
度假區的農家樂生意剛有點起色,我卻發現賬目不對勁。合夥人小王總是支支吾吾,說資金被“上面”調走了。我私下查了賬,發現幾筆大額款項流向了一家註冊在深圳的空殼公司,法人是個叫“張志國”的人。
我試着問老李,他只嘆氣:“別瞎折騰,有些人你惹不起。”那天晚上,我被叫到項目部的臨時辦公室。老大從北京來了,坐在昏暗的燈光下,面前擺着一瓶沒開封的飛天茅臺。他穿着一件不起眼的灰色夾克,眼神卻像刀子一樣鋒利。
我站得筆直,像在順義學院列隊時那樣,額頭冒汗。“小周,”老大點了一支菸,吐出一口白霧,“你幹得不錯,但太聰明瞭。”他頓了頓,語氣平靜得嚇人,“度假區的事,上面很關注。你查賬的勁兒,我欣賞,但別查過頭。”我低着頭,沒敢接話。
空氣裏只有菸草的焦味和牆上掛鐘的滴答聲。老大忽然笑了,拍了拍我的肩膀:“你知道我爲什麼帶你進這行嗎?因爲你沒根沒底,乾淨。像你這樣的人,最好用,也最危險。”
那天,他沒多說,但臨走前留下一句話:“記住,這世上有些門,開了就關不上。”我愣在原地,直到他的車消失在夜色裏。
幾天後,老李偷偷塞給我一份泛黃的複印件,是一份20年前的軍方檔案,關於一個叫“張志國”的軍官。檔案裏提到,張志國曾在90年代擔任某軍區後勤部副部長,負責裝備採購和軍用土地開發,立過二等功,但在2003年因“個人原因”退役。
照片上的張志國年輕英武,眉眼間和老大有幾分相似。老李壓低聲音:“這人就是你老大,當年他在軍裏可是個傳奇。聽說他搞定了好幾個大項目,軍區的訓練基地、邊境的物流線,都是他一手操辦。可惜,風頭太盛,樹敵太多,有人舉報他挪用軍資,差點沒出來。”
我心跳加速,檔案裏提到的“個人原因”模糊不清,但字裏行間能嗅到腐敗的味道。
2003年退役,正好是軍隊大規模清理商業化的時候,類似徐才厚、郭伯雄這樣的軍方大佬後來都被查出利用後勤和採購斂財。
老大顯然更聰明,提前抽身,帶着一身人脈和財富轉入地下。老李警告我:“別再挖了。張志國現在是棵大樹,根深蒂固,動他等於自找死路。”
我嘴上答應,心裏卻下定決心,要弄清楚老大的底細。
24年秋,我接到老大的電話,要求我回北京“交代問題”。我沒去,而是把U盤的副本寄給了南京的一位記者朋友,叮囑他匿名爆料。幾天後,度假區的爛尾醜聞上了熱搜,幾個管理層被紀委帶走,但老大的名字一次也沒出現。我知道,這只是捅了馬蜂窩,真正的風暴還在後面。
果然,一個月後,我在江西的飯館迎來了一位不速之客。那天雨下得很大,一個穿黑色風衣的中年男人推門進來,點了一碗麪,慢條斯理地喫着。
我認出他是順義學院的教官老陳,曾經教我格鬥的那位。他喫完,擦了擦嘴,遞給我一張機票:“老大讓你去北京,別逼我動手。”我沒接票,盯着他問:“老大到底是誰?張志國,還是別的什麼人?”老陳冷笑:“你知道得夠多了,聰明人該學會閉嘴。”我被押上車,帶到北京順義學院。
學院還是那副冷清的樣子,但鐵門後的氣氛更加森嚴。老大站在訓練場的中央,身旁站着幾個陌生面孔,有西裝革履的商人,也有眼神陰鷙的安保人員。
我被帶到一間地下室,四面牆都是水泥,沒有窗戶。老大沒廢話,開門見山:“你寄的材料,差點壞了大事。”他從桌上拿起一疊照片,扔在我面前。照片裏是我在南京查賬的監控截圖,還有幾張是我在深圳別墅時偷錄音頻的畫面。
我心頭一沉,他早就盯着我。“你想知道我是誰?”老大點了一支菸,語氣平靜,“好,我告訴你。90年代,我在軍裏管後勤,建了半個邊境的軍工線,上面誇我能幹,下面敬我三分。可惜,這世道不讓好人活,有人想拿我開刀,我只好退了。退了以後,我沒閒着,搭了個臺子,讓大家繼續唱戲。”
他頓了頓,目光如刀:“你以爲度假區那點錢是我要的?那只是個餃子,上面的人喫飽了,纔有下面的路。你壞了規矩,連累的不是我,是整個鏈子。”
從老大的話裏,我拼湊出他的全貌。他叫張鵬,化名張志國,70年代入伍,90年代在軍區後勤部嶄露頭角,靠着過硬的業務能力和“關係”,拿下多個軍工合同,積累了第一桶金。
但2000年代初,軍隊反腐風聲漸緊,他被舉報挪用軍資,險些鋃鐺入獄。關鍵時刻,他通過高層關係“平安着陸”,退役後轉入商界,成立了一家名爲“華安國際”的安保公司,表面提供高端安保服務,實則爲他的權力交易提供掩護。
退役後,他依然與軍方高層保持聯繫,通過“國際防衛安全學院學院”培訓現役軍人的親屬,爲軍工項目牽線搭橋。與黑石集團的合作,通過華安國際在海外的空殼公司,參與中東或非洲的能源項目,清洗國內的灰色資產。
老大在深圳的別墅是他的“交易中心”,與地方國企(如深圳國資委)、科技巨頭(如TCL關聯企業)合作,佈局房地產和基建。他的茅臺、古董和字畫,是政商圈的“潤滑劑”,都反映了他與高官商人的密切關係。
老大的“組織”不僅限於國內,還通過僱傭兵培訓(我遇到的伊拉克僱傭兵白曉保)參與國際安保市場,涉及“一帶一路”沿線的項目保護。他的順義學院不僅是培訓基地,還爲海外任務輸送人才。
老大並非單純的冷血掮客。他說“有人想拿我開刀”,他退役時揹負冤屈,或許曾因軍功自視甚高,卻被權力鬥爭犧牲。
這讓他對體制既忠誠又戒備,決心打造自己的帝國。他對我的“欣賞,可能因爲我讓他看到年輕時的自己,但我的背叛也讓他感到威脅。
老大掐滅菸頭,語氣冰冷:“你有兩條路,一條是跟我走,去俄羅斯,幫我盯着那邊的生意;另一條,你知道後果。”
我盯着他,腦海裏閃過深圳別墅的奢華、南京工地的憤怒,以及老家飯館裏母親的白髮。我問:“俄羅斯那邊的生意,是不是跟洗錢有關?還是別的什麼?”老大眯起眼,笑了:“你真不該問這個。”
他揮手,老陳上前,給我看了一份文件,上面的人,已經批了幾個大項目,涉及中俄邊境的能源和軍工。你要是不配合,連你家那小飯館都保不住。”
那一刻,我明白了,老大不是一個人,他身後的網,深到連他自己都只是其中一環。
我想起U盤裏的錄音,裏面有他在深圳別墅與一位高官的對話,提到“邊境線上的貨”和“北邊的朋友”。如果我把這交給警方,也許能扳倒他,但也可能毀了自己和家人。
我假意答應,爭取時間脫身。那夜,我趁看守換崗,偷了老陳的車,逃出學院,連夜趕往南京,找到那位記者朋友。我把U盤交給他,叮囑他匿名投給中紀委,同時自己買了一張去南方的火車票,準備徹底消失。
24年冬,新聞報道了一起跨國洗錢案,涉及中俄邊境的能源交易,數名高官落馬,但老大的名字依然沒出現。我躲在雲南邊境的小鎮,開了一家無名小店,時刻提防有人找上門。
偶爾,我會收到匿名短信,內容只有四個字:“老大看着你。”
老大的背景讓我意識到,他不僅是退役少將,更是一個時代的縮影——在權力、財富和風險的夾縫中,他建了個隱形帝國,卻也讓自己成了棋盤上的卒。
他的軍旅生涯賦予了他資源和野心,但也讓他揹負了無法洗白的陰影。我的選擇,捅破了他的網,卻也讓我永遠活在陰影裏。
小鎮的清晨被霧氣籠罩,我站在無名小店的門口,端着一碗米線,目光掃過街角。半個月前,我把U盤交給南京的記者朋友,裏面有老大在深圳別墅的錄音,提到“北邊的朋友”和“邊境線上的貨”。新聞爆出中俄邊境的洗錢案後,我以爲老大會被牽連,但他的名字從未出現。
我知道,他太狡猾,早就把自己藏在迷霧裏。昨天,店裏來了個操外國口音的顧客,點了一杯咖啡,臨走時留下一張紙條:“張鵬讓你別亂跑。”
紙條上的字跡歪歪扭扭,像臨時寫的。我燒了紙條,背上行囊,準備換個地方藏身。U盤的備份還在我身上,那是唯一的護身符,也是最大的危險。
老大的國際聯繫,是我在順義學院和深圳別墅時零星聽來的片段。伊拉克僱傭兵白曉保曾提到“中東的單子”,深圳別墅的會客廳裏,偶爾會出現操英語的西裝男,談及“海外賬戶”和“能源項目”。
我一直以爲這些是老大的生意經,直到南京項目的賬目讓我意識到,他可能在玩一場更大的遊戲——一場跨越國界的權力與金錢交易。
那是個悶熱的夜晚,別墅負一樓的會客廳燈火通明,我端着剛做好的川味水煮魚,推門進去。
老大坐在主位,身旁是個金髮碧眼的外國人,穿着剪裁得體的西裝,旁邊放着一個黑色公文包。桌上擺着幾瓶飛天茅臺,還有一摞文件,封皮上寫着“Blackstone Energy Partners”。
我低頭擺菜,耳朵卻豎得老高。“張先生,”金髮男用流利的中文說,“中東的油田項目需要你們的人手,安全保障得跟上。資金已經到位,迪拜的賬戶隨時可以走。”
老大點了一支菸,淡淡道:“人沒問題,學院那邊剛訓出一批,俄語、阿拉伯語都會。但你得保證,北邊的線不能斷。”金髮男笑了笑,壓低聲音:“黑石集團從不失手。莫斯科那邊已經點頭,貨走海參崴,乾淨得很。”
我退出房間,心跳如鼓。海參崴?中東油田?這些詞在我腦子裏炸開。
我想起順義學院的白曉保,他教我健身時無意中透露的: 好的,我明白。
老大的國際聯繫遠比我想象的複雜。他退役少將的身份只是起點,真正的帝國是他退役後用軍方人脈和資源搭建的跨國網絡。
順義學院不僅是國內安保人員的培訓基地,還爲海外任務輸送精銳,涉及中東、非洲和俄羅斯的敏感項目。
他的“華安國際”公司,表面上是安保服務商,實則是國際交易的掩護,核心業務包括:
中東安保業務,通過與黑石集團的合作,老大爲中東油田和基建項目提供武裝護衛。這些項目多與“一帶一路”倡議相關,涉及沙特、阿聯酋等國的能源開發。白曉保曾透露,他在伊拉克護送過油氣管道的運輸車隊,任務由華安國際承接,背後有老大的影子。
老大的網絡延伸到俄羅斯遠東地區,涉及能源貿易和軍工物資的“灰色運輸”。錄音中提到的“邊境線上的貨”,通過海參崴港走私的電子元件或稀有金屬,繞過西方制裁,用於中俄的軍工合作。這些交易通過離岸公司洗錢,資金流向迪拜或新加坡的賬戶。
順義學院培訓的僱傭兵不僅服務於國內客戶,還被派往非洲和中東,參與礦產資源保護或衝突地區的“特殊任務”。這些人員多是退役特種兵,精通多國語言,紀律嚴明,忠誠於老大。
老大與黑石集團的合作,是通過華安國際的空殼公司在海外投資房地產或能源項目,清洗國內的灰色收入。他的別墅裏堆滿的茅臺和古董,部分是海外客戶送的“禮物”,如俄羅斯的伏特加和中東的黃金工藝品。
老大的國際聯繫並非一帆風順。現實中,“一帶一路”項目常面臨地緣政治風險,如西方國家的反洗錢調查和俄羅斯內部的派系鬥爭。老大的生意需要在多方勢力間平衡,既要討好國內高層,又要應對國際監管,還要提防俄羅斯或中東合作伙伴的“背刺”。
25年春,我藏在雲南小鎮,卻被老陳找到,押回北京順義學院。我被捆綁在地下室的審訊室裏,老大坐在我對面,身後站着兩個陌生人,一個操俄語口音的中年男人,另一個是西裝革履的華人,眼神陰冷。
老大扔出一份文件,封面上是“華安國際”的 logo,裏面是中俄邊境交易的流水記錄,涉及一家註冊在開曼羣島的公司。“你以爲把U盤給記者就完了?”老大冷笑,“你動的,是北邊的線。那邊的人可沒我這麼好說話。”我愣住了。
錄音裏提到的“北邊的朋友”,原來不是國內高官,而是俄羅斯的某個寡頭,控制着海參崴的運輸線。文件顯示,華安國際通過黑石集團的迪拜賬戶,爲俄羅斯採購了禁運的芯片,價值數億美元。
老大的角色是中間人,拿了鉅額佣金,但交易被西方情報機構盯上,美國的OFAC(外國資產控制辦公室)已經開始調查。
“你有兩條路,”老大點了一支菸,語氣平靜,“一是去俄羅斯,幫我穩住那邊的人,證明你的忠誠;二是留下,記者那點料,夠你家破人亡。”我嚥了口唾沫,腦子裏亂成一團。去俄羅斯,等於跳進另一個火坑,可能捲入更危險的國際博弈;留下,我知道老大的手段,江西的小飯館恐怕保不住。
更糟的是,U盤裏的錄音已經引發連鎖反應,南京的記者朋友告訴我,中紀委和公安部聯合調查,幾個度假區高管供出了老大的名字,但證據不足,他依然逍遙法外。
兩天後,我被帶到北京郊區的一棟隱祕別墅。老大不在,但來了個新面孔——一個自稱“詹姆斯”的英國人,操着一口流利中文。他自稱是黑石集團的代表,實則是西方情報機構的線人。
他開門見山:“張的生意,踩了紅線。OFAC查到迪拜賬戶的資金流,你手裏的錄音,是我們需要的最後一塊拼圖。”詹姆斯遞給我一張瑞士銀行的卡,裏面有500萬美金,條件是交出U盤,並作爲證人出庭,指控老大的洗錢網絡。
我盯着那張卡,心跳加速。500萬,夠我下半輩子衣食無憂,但也意味着徹底背叛老大,背叛那個曾讓我敬畏的“帝國”。我問:“如果我拒絕呢?”詹姆斯冷笑:“你以爲張鵬護得了你?他自己都泥菩薩過江。俄羅斯那邊已經有人想拿他開刀,換取跟西方的交易籌碼。”
我腦子裏閃過老大在深圳別墅的畫面,他曾說:“這世上有些門,開了就關不上。”
現在,我站在那扇門前,進退兩難。交出U盤,我可能被老大的網絡追殺;拒絕,我可能被西方勢力或俄羅斯的“朋友”盯上。更別提國內的反腐調查,隨時可能把我當作替罪羊。
當晚,我被關在別墅的地下室,門外是老陳和幾個僱傭兵。我趁夜深,用從順義學院學的技巧,撬開一扇通風窗,逃了出去。
我連夜趕到昆明,找到一個老同學,借了他的身份證買了張飛往泰國曼谷的機票。在機場,我把U盤的備份上傳到一個加密雲盤,設置了定時發送給中紀委和國際刑警組織,如果我72小時內沒取消,文件會自動公開。
在曼谷的廉價旅館裏,我收到一封匿名郵件,附件是一張照片:我母親在江西小飯館門口,被一個陌生人尾隨。我心如刀絞,知道這是老大的警告。我撥通詹姆斯的電話,告訴他:“我給你U盤,但我要安全通道,送我去第三國。”詹姆斯答應了,但條件是我必須在國際法庭上作證,指控老大的洗錢網絡。
幾天後,我被祕密送往新西蘭,住進一個偏僻小鎮的保護屋。U盤裏的錄音成爲國際刑警組織和OFAC的突破口,華安國際的迪拜賬戶被凍結,老大的幾個海外合夥人被捕。
但老大依然像幽靈,銷聲匿跡,只留下一句通過老陳傳來的話:“你跑得再遠,也逃不出我的手。”
25年夏,我在新西蘭的小鎮上開了一家咖啡館,化名生活,時刻提防有人敲門。新聞裏,華安國際被查封,老大的名字終於出現在中紀委的通報中,但指控僅限於國內的腐敗案,國際交易的部分被大事化小。
我知道,他可能通過俄羅斯或中東的關係,轉移了資產,藏在某個無人知曉的角落。
老大的國際聯繫,是一張橫跨中東、俄羅斯和西方資本的網,每一根線都沾着血與金。他的軍方背景讓他遊刃有餘,但也讓他成爲多方勢力的靶子。
我的揭露,撕開了一個口子,卻遠不足以摧毀他的帝國。我每天打開電腦,檢查那個加密雲盤,提醒自己:真相有代價,但沉默的代價更大。
每天清晨,我在廚房裏忙碌,切菜、炒菜、調湯,熟悉的油煙味讓我感到踏實。餐館不大,但生意還算穩定,街坊鄰居喜歡來這裏喫一碗熱騰騰的雜醬麪,誇我的手藝好。
每當聽到這些,我都會心一笑,想起在深圳別墅裏爲高官大商做菜的日子。
那時的我,滿心想着出人頭地;如今的我,只想守住這一方小小的天地。
偶爾夜深人靜,我會翻出手機,看看當年的照片:順義學院的訓練場,深圳別墅的茅臺酒瓶,還有南京項目工地上的黃土。
我想起老大那張深不可測的臉,想起白曉保爽朗的笑聲,想起徐峯冷嘲熱諷的眼神。這些記憶像刀子一樣鋒利,卻也讓我更加珍惜現在的平靜。
現實教會了我,天花板從來不是觸手可及的夢想,而是無數慾望與陰謀交織的陷阱。我選擇了平凡,選擇了自由,也選擇了與過去的自己和解。或許,這纔是真正的救贖。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