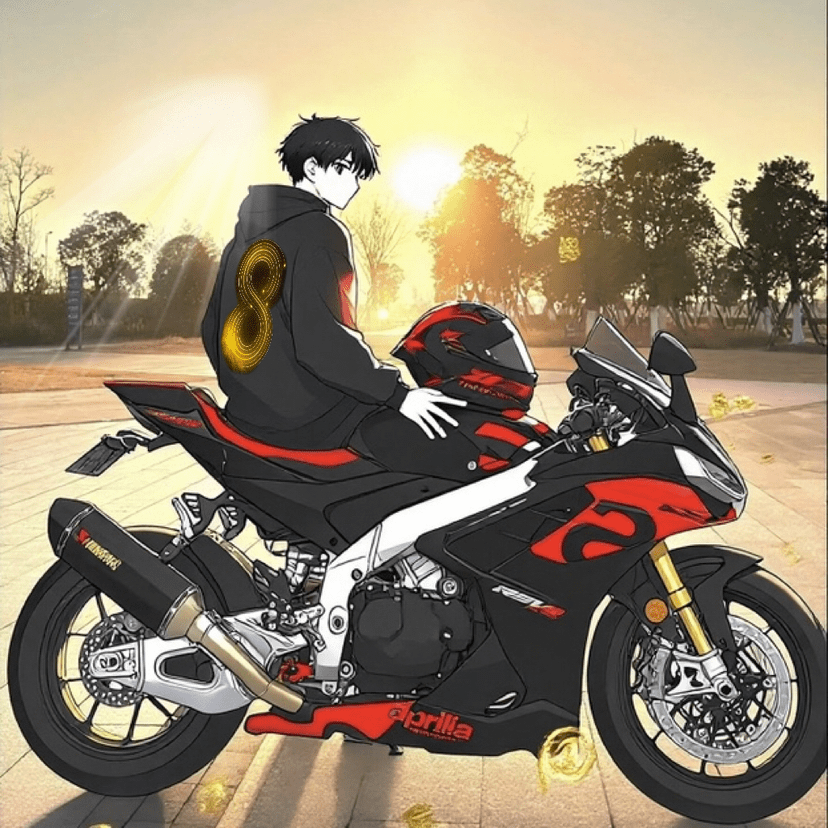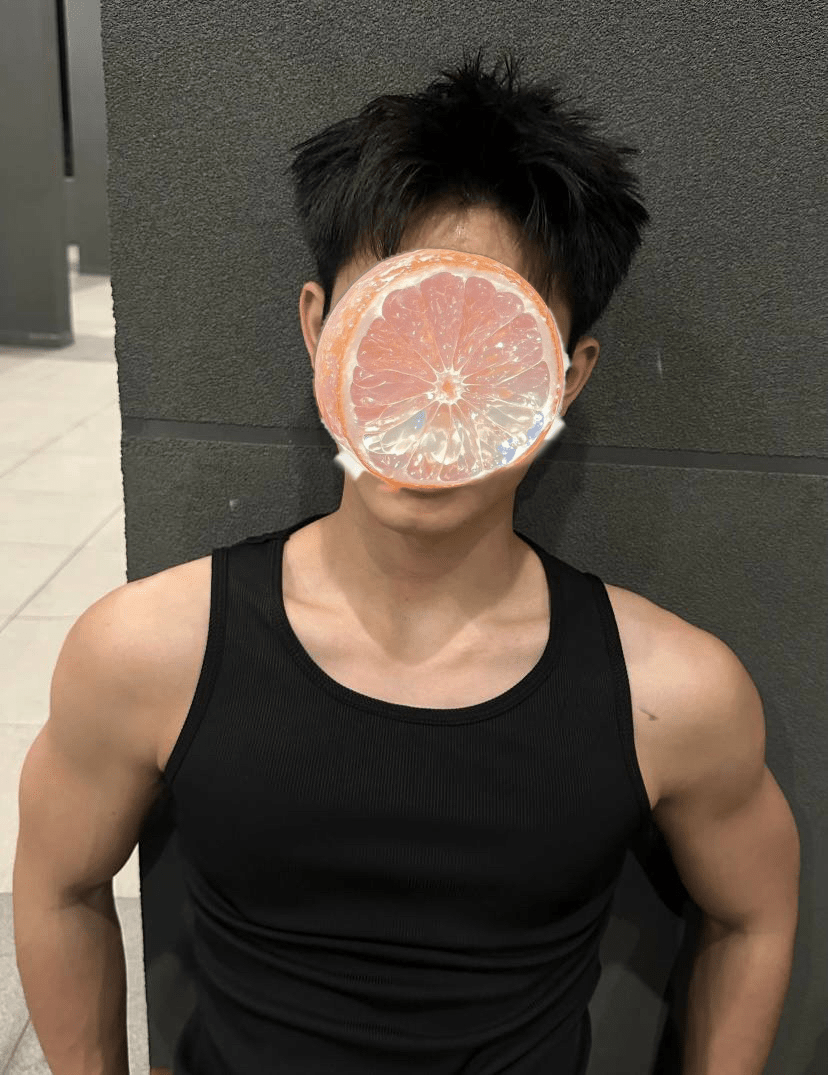本文由 @SafePal 赞助
@万联welinkBTC 创作
我将讲诉我的离奇经历,我在大佬手下的真实故事!
22年我从江西吉安一上市公司副总离职,青年得志,总想大展宏图,又明白自己不过是一个三无人员,无背景,无人脉,无资金,就经过几轮介绍,在北京见到一位退役少将。
一开始我也以为电视里的骗局,我几经查证确实真实,然后拜入门下,我以为我终于触碰到国内的天花板,故事才刚刚开始。
开始他们也对我抱有隔阂,问我愿不愿意加入他们,愿意的话可能要抛弃很多,我当时已经忘记了一切,我答应了,我进入到北京顺义,一个由监狱改造的学校,国际防卫安全学院,进行全封闭管理训练,没收手机,部队化训练,有安全防卫,暗杀,搏杀,射击,我的车技身体都在里面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还经常会遇到全球各地回来的雇佣兵,其中伊拉克雇佣兵白晓保还教过我健身,我的世界观,遭遇极大的冲击,因为它们跟黑石集团有合作,我一度以为自己也会走上这条路。
半年后的一天,监狱大门打开,我已经跟社会失去了半年联系,后面开始逐步融入他们的组织,执行一些简单任务。又过了3个月我终于再见到那位大佬,不过我们都喊他老大。
从北京3辆商务奔袭深圳,在南山区一个别墅里,我开始了我的魔幻经历。
奔袭到南山区TCL 园区旁的别墅,路口是深圳驻香港的一些部队大院。
我们一班是 3 个人平常负责生活起居,特殊的情况也要处理一些问题,平常负责生活起居也要照顾大家的日常吃饭,我也是在这个时候练就了一手好厨艺,基本上天南地北的菜都会做,因为经常要宴请客人。
光吃喝往来已经让我跌破眼睛,老大不喝酒却很有很多人送酒飞天茅台都是几十件起送,其中不乏 30 年 70 年茅台,让我开了眼界的是茅台居然还有金币金杯金钥匙,晚上拿到手机去查价格的时候一瓶就近 70 万,别墅的负二楼只有我刚到时打扫卫生,搬古董的时候才去过,一眼望去,全是古董字画,然后就再也没下去过。
然而我们 9 个卫士只能住在别墅的顶楼仓储间,但也比在学院的时候轻松很多,也自由些,有时候还能偶尔出去吃一顿自己想吃的,体能训练也只有每日早晚各一次 3 公里。
就在深圳的几个月里我迎来了新年,每日工作大多就是安排日常生活,当司机,出门的时候做安保,短短几个月见到太多太多高官大商。
我也是在这个时候崭露头角,因为我的手艺比较好,很多时候来客人也是我做饭,我也会猜想一下客人,主人的喜好,也是慢慢获得了一些信任,也去负责了一些更隐秘的工作。
原来这些大佬也有大佬的问题,不过是我托你帮忙,你托我帮忙,有部队想要升职的,有走私被抓想疏通关系的,有想接部队工程的,有想为儿子铺路的太多太多。
在广州酒店时,遇到一位现在已经落马的部队高官,当时被查很紧张,到处在谋求关系想要脱生,然而我们老大也是手眼通天,原来他也只是一个关卡,上面还有更重要的人。
也是在这个时候我们这一波人要被分开去几个地方负责各自的工作线,有三个可以挑选去的地方,俄罗斯,缅甸,南京,我一开始想去俄罗斯,因为可以见识到更大的天地,不过也是真的危险,在我们从新回到北京的时候,我们被安排了一场问话,也就是这场问话,让我确定了接下来两年的人生。
那天我们还在北京顺义的学院里,训练中说是老大要来,我们穿戴整齐在学院门口列队迎接。
然后就是按顺序进行谈话,一开始就是问问怎么样,有没有想法,想去哪里,聊聊天就下一个人,当时我一心想闯出一番天地,谈话中我说我想去俄罗斯,不仅能出国而且会安排大学进行学习,虽然远和辛苦一些,但总是能够换一番天地,结果并不如我所愿。
后续安排是我去了南京六合区,当地一个深圳国资委下属企业在南京六合区进行项目开发,我也顺理成章去任职,项目可查现在已经烂尾,六合区的一个温泉度假区。
这个时候已经 23 年的春夏时节,那时候地产已经寒冬,老大过去接手注资 3 个亿看能不能救活项目,其中牵扯太多,几方人马在争夺国家资产,没有一个人关心项目到底能不能活。
我也是在这个时候鬼迷心窍,做了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事情,进驻项目后,有钱了大家都很开心,光光在我负责的区域内我都能够感受到资金在大量被浪费,这也是后来问题爆发的其中之一。
因为我之前在阿里负责过各类商业运营,当时度假区内还没有饭店,老大也让我负责开一家农家乐,一是解决接待吃饭问题,二是工地确实无聊得弄点乐趣,其中牵扯就开始了。
当时我与老大下属一个公司合资进行承包一些度假区内的零散业务,其中包括农家乐,垂钓园,超市,露天酒吧等等,当时想法很美好,结局很悲惨。
也就是抱着美好的愿望我在短短一年内破产了。
项目烂尾的阴霾笼罩着整个六合温泉度假区,曾经的宏伟蓝图如今只剩一堆钢筋水泥和无人问津的空地。我站在农家乐的门口,看着远处工地上一片狼藉,心中的滋味难以言喻。
一年前,我满怀憧憬来到这里,以为能借着老大的资源和自己的能力闯出一片天,却没想到,这片土地成了我的滑铁卢。
农家乐、垂钓园、超市、露天酒吧——这些看似简单的生意,却因为层层利益纠葛和我的天真判断,变成了吞噬我所有积蓄的无底洞。
合资公司的合伙人表面上对我笑脸相迎,背地里却在账目上动手脚,度假区的管理层对我的“外来户”身份充满戒心,工地上的工人因为拖欠工资时常闹事,而我夹在中间,成了众矢之的。
更糟糕的是,老大的3亿注资并没有如预期般救活项目。资金像流水一样被各种关系户和中间人瓜分,真正用到项目上的少之又少。
我开始怀疑,老大让我来南京,根本不是为了让我建功立业,而是把我当作一枚棋子,用来平衡各方利益。
在南京六合区的温泉度假区项目中,我的生活仿佛被按下了快进键。表面上,我是老大团队的一员,负责度假区内农家乐、垂钓园、超市等业务的运营,看似风光无限,实则暗流涌动。
项目的背后,是多方势力角逐的复杂棋局:深圳国资委、地方官员、地产开发商、甚至一些隐秘的“掮客”,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利益博弈。
而我,一个曾经意气风发的青年,如今却在这一场场博弈中逐渐迷失。
23年秋天,事情开始急转直下。一天晚上,我接到一个匿名电话,对方压低声音警告我:“别再查账了,有些东西不是你能碰的。”
我愣住了,最近我确实在核查农家乐和超市的账目,发现不少资金流向不明,合伙人总是以“公关费用”搪塞我。
我本想上报老大,但电话让我意识到,这背后可能牵扯到比我想象中更大的利益网。与此同时,度假区的工人开始大规模停工,数百人堵在项目部门口,要求兑现拖欠的工资。管理层把责任推到我头上,称是我负责的“配套设施”收入不足,导致资金链断裂。我试图解释,但没人听我的。
工人们的情绪越来越激动,有人甚至砸了农家乐的玻璃。我站在人群前,试图安抚,却被一个愤怒的工人指着鼻子骂:“你个外地人,拿我们的血汗钱去挥霍!”
那一刻,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立。曾经在深圳别墅里为高官大商烹饪美食的我,如今却被一群愤怒的工人围困,身后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为我说话。
温泉度假区项目启动之初,3亿元的注资让所有人眼红。表面上,这笔钱是为了“救活”项目,但实际上,大部分资金被迅速瓜分。施工方虚报工程量,供应商提供劣质材料,管理层中饱私囊,甚至连我负责的农家乐和垂钓园项目,都被要求“配合”某些关联公司的账务操作。
我试图保持底线,但很快发现,拒绝参与意味着被边缘化,而参与则让我越陷越深。
与此同时,我与老大的一个亲信——一个叫徐峰的副手,产生了直接冲突。徐峰是老大的“老兄弟”,40多岁,精明而强势,负责项目的财务审批。
他看不上我这个“外来者”,认为我不过是老大一时兴起提拔的小角色。他多次在会议上公开质疑我的运营方案,甚至暗示我的农家乐项目“吃回扣”。我试图解释,农家乐的亏损是因为初期投入过大、客流量不足,但他根本不听,反而要求我将部分业务外包给他的“关系户”。
有一次,我在农家乐的账目中发现一笔异常支出:一笔标明“设备维护”的50万元款项,实际上流向了一家空壳公司。我追查下去,意外发现这家公司与徐峰的亲戚有关。
我将此事私下向老大汇报,希望得到支持,却没想到老大的反应出奇冷淡:“小李,有些事你别管,做好你自己的就行。”这句话让我心头一凉,我开始意识到,即便是老大,也未必完全信任我。
度假区项目不仅内部矛盾重重,外部的阻力也接踵而至。
六合区的温泉度假区本是当地政府招商引资的重点项目,但随着地产寒冬的到来,地方官员的态度开始暧昧。一些官员希望通过项目捞取好处,另一些则对深圳国资委的强势介入不满,暗中支持本地开发商制造麻烦。
有一次,农家乐刚开业不久,当地一家“地头蛇”性质的餐饮公司找到我,声称我“抢了他们的生意”,要求我支付一笔“保护费”,否则就让我的店开不下去。我拒绝了他们的要求,结果第二天,农家乐的食材供应商突然停止供货,理由是“收到了匿名威胁”。我试图通过老大的关系疏通,却发现这些地头蛇背后竟然也有高层的影子。徐峰甚至冷嘲热讽:“小李,你不是很能干吗?怎么连这点小事都搞不定?”
在内外夹击下,我的处境越来越艰难。农家乐、垂钓园等业务的亏损日益严重,资金链几近断裂。我试图通过优化运营、引入新菜品、举办活动来吸引客流,但效果甚微。
更糟糕的是,我发现自己当初与老大下属公司合资的合同中,隐藏着不平等条款:一旦项目亏损,我个人需要承担大部分债务,而对方几乎没有风险。
2023年秋天,项目彻底陷入停滞。3亿元的注资早已被挥霍一空,度假区的温泉酒店主体建筑成了烂尾楼,工人们纷纷讨薪,供应商上门追债。我的农家乐和垂钓园也因资金链断裂而关门,超市和露天酒吧更是连开业的机会都没有。
我背上了近200万元的债务,个人账户几乎被清空,连租住的小公寓都付不起房租。更让我崩溃的是,老大在这个时候突然“失联”。我试图联系他,却被告知他已前往海外“处理事务”。
徐峰则趁机对我落井下石,散布谣言称我“私吞上了”项目资金,导致项目失败。我试图向学院的负责人求助,却只得到一句冷冰冰的回复:“你自己惹的麻烦,自己解决。”
在最绝望的时刻,我收到了一封匿名邮件。邮件里是一些关于徐峰和地方官员勾结的证据,包括账目记录、录音片段,甚至几份秘密合同的扫描件。寄件人没有署名,只留下一句话:“想翻身,就用好这些。”
我犹豫了整整三天。使用这些证据,意味着彻底与徐峰、甚至整个组织翻脸,风险巨大;但如果什么都不做,我不仅要背负巨额债务,还可能被彻底踢出局,甚至面临更严重的后果。我开始暗中调查,联系了几个在学院时的老战友,试图拼凑出真相。
同时,我也找到了一位在南京的旧友——一位在媒体行业工作的记者,名叫张然。他告诉我,六合区的项目背后牵涉更大的利益网络,徐峰只是其中一环,而真正的“大鱼”可能指向更高层的某些人物。
2023年冬,我决定孤注一掷。我将证据整理后,匿名交给张然,由他在媒体上曝光。与此同时,我联系了深圳国资委的一位老同事,暗示项目资金被挪用的情况。几天后,徐峰被调查的消息传出,地方几名官员也因“经济问题”被带走询问。温泉度假区的项目彻底停摆,但我的债务问题却因资金追回而得到部分缓解。
然而,这场胜利代价高昂。我彻底失去了老大的信任,组织内部开始对我冷处理。我知道,自己不可能再回到那个圈子。
2024年初,我悄然离开南京,回到江西老家,带着一身疲惫和少得可怜的存款,开始重新规划人生。
回到吉安,我开了一家小小的餐馆,凭借在深圳练就的厨艺,生意勉强维持。过去的经历像一场梦,魔幻而危险。我偶尔会想起在北京顺义的训练场,想起那些雇佣兵的面孔,想起老大别墅里堆满的茅台和古董。但更多时候,我庆幸自己还能站在阳光下,过着普通却踏实的生活。
现实告诉我,所谓的天花板,从来不是触手可及的。它背后,是无数交织的利益、背叛和风险。而我,最终选择了平凡,却也选择了自由。
夜深了,小饭馆的最后一桌客人醉醺醺地离开,我擦着桌子,目光落在墙角的旧电视上。新闻里正在报道南京六合温泉度假区的烂尾事件,几名官员被带走调查,但语焉不详。
我心头一紧,关掉电视,锁上门,回到后厨的小隔间。那张从南京带回的U盘,藏在床板下的暗格里,里面是度假区账目的副本,还有一些我在深圳别墅偷录的对话片段。
我本以为逃回江西老家,就能甩掉那段魔幻人生,但老大的影子如影随形。
半个月前,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短信:“别以为躲起来就没事了,老大让你回北京。”我没回,换了卡,却总觉得有人在暗中盯着我。昨天,饭馆对面的烟酒店老板无意提起,最近有个穿西装的陌生人打听我的底细。
我点上一支烟,思绪回到南京六合的最后几个月。那时,我隐约察觉老大不是简单的退役少将,他的背景像一张巨大的网,笼罩着我,也让我窒息。
今晚,我决定再听一遍U盘里的录音,也许能找到些线索,弄清楚老大到底是谁,到底想要什么。
度假区的农家乐生意刚有点起色,我却发现账目不对劲。合伙人小王总是支支吾吾,说资金被“上面”调走了。我私下查了账,发现几笔大额款项流向了一家注册在深圳的空壳公司,法人是个叫“张志国”的人。
我试着问老李,他只叹气:“别瞎折腾,有些人你惹不起。”那天晚上,我被叫到项目部的临时办公室。老大从北京来了,坐在昏暗的灯光下,面前摆着一瓶没开封的飞天茅台。他穿着一件不起眼的灰色夹克,眼神却像刀子一样锋利。
我站得笔直,像在顺义学院列队时那样,额头冒汗。“小周,”老大点了一支烟,吐出一口白雾,“你干得不错,但太聪明了。”他顿了顿,语气平静得吓人,“度假区的事,上面很关注。你查账的劲儿,我欣赏,但别查过头。”我低着头,没敢接话。
空气里只有烟草的焦味和墙上挂钟的滴答声。老大忽然笑了,拍了拍我的肩膀:“你知道我为什么带你进这行吗?因为你没根没底,干净。像你这样的人,最好用,也最危险。”
那天,他没多说,但临走前留下一句话:“记住,这世上有些门,开了就关不上。”我愣在原地,直到他的车消失在夜色里。
几天后,老李偷偷塞给我一份泛黄的复印件,是一份20年前的军方档案,关于一个叫“张志国”的军官。档案里提到,张志国曾在90年代担任某军区后勤部副部长,负责装备采购和军用土地开发,立过二等功,但在2003年因“个人原因”退役。
照片上的张志国年轻英武,眉眼间和老大有几分相似。老李压低声音:“这人就是你老大,当年他在军里可是个传奇。听说他搞定了好几个大项目,军区的训练基地、边境的物流线,都是他一手操办。可惜,风头太盛,树敌太多,有人举报他挪用军资,差点没出来。”
我心跳加速,档案里提到的“个人原因”模糊不清,但字里行间能嗅到腐败的味道。
2003年退役,正好是军队大规模清理商业化的时候,类似徐才厚、郭伯雄这样的军方大佬后来都被查出利用后勤和采购敛财。
老大显然更聪明,提前抽身,带着一身人脉和财富转入地下。老李警告我:“别再挖了。张志国现在是棵大树,根深蒂固,动他等于自找死路。”
我嘴上答应,心里却下定决心,要弄清楚老大的底细。
24年秋,我接到老大的电话,要求我回北京“交代问题”。我没去,而是把U盘的副本寄给了南京的一位记者朋友,叮嘱他匿名爆料。几天后,度假区的烂尾丑闻上了热搜,几个管理层被纪委带走,但老大的名字一次也没出现。我知道,这只是捅了马蜂窝,真正的风暴还在后面。
果然,一个月后,我在江西的饭馆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那天雨下得很大,一个穿黑色风衣的中年男人推门进来,点了一碗面,慢条斯理地吃着。
我认出他是顺义学院的教官老陈,曾经教我格斗的那位。他吃完,擦了擦嘴,递给我一张机票:“老大让你去北京,别逼我动手。”我没接票,盯着他问:“老大到底是谁?张志国,还是别的什么人?”老陈冷笑:“你知道得够多了,聪明人该学会闭嘴。”我被押上车,带到北京顺义学院。
学院还是那副冷清的样子,但铁门后的气氛更加森严。老大站在训练场的中央,身旁站着几个陌生面孔,有西装革履的商人,也有眼神阴鸷的安保人员。
我被带到一间地下室,四面墙都是水泥,没有窗户。老大没废话,开门见山:“你寄的材料,差点坏了大事。”他从桌上拿起一叠照片,扔在我面前。照片里是我在南京查账的监控截图,还有几张是我在深圳别墅时偷录音频的画面。
我心头一沉,他早就盯着我。“你想知道我是谁?”老大点了一支烟,语气平静,“好,我告诉你。90年代,我在军里管后勤,建了半个边境的军工线,上面夸我能干,下面敬我三分。可惜,这世道不让好人活,有人想拿我开刀,我只好退了。退了以后,我没闲着,搭了个台子,让大家继续唱戏。”
他顿了顿,目光如刀:“你以为度假区那点钱是我要的?那只是个饺子,上面的人吃饱了,才有下面的路。你坏了规矩,连累的不是我,是整个链子。”
从老大的话里,我拼凑出他的全貌。他叫张鹏,化名张志国,70年代入伍,90年代在军区后勤部崭露头角,靠着过硬的业务能力和“关系”,拿下多个军工合同,积累了第一桶金。
但2000年代初,军队反腐风声渐紧,他被举报挪用军资,险些锒铛入狱。关键时刻,他通过高层关系“平安着陆”,退役后转入商界,成立了一家名为“华安国际”的安保公司,表面提供高端安保服务,实则为他的权力交易提供掩护。
退役后,他依然与军方高层保持联系,通过“国际防卫安全学院学院”培训现役军人的亲属,为军工项目牵线搭桥。与黑石集团的合作,通过华安国际在海外的空壳公司,参与中东或非洲的能源项目,清洗国内的灰色资产。
老大在深圳的别墅是他的“交易中心”,与地方国企(如深圳国资委)、科技巨头(如TCL关联企业)合作,布局房地产和基建。他的茅台、古董和字画,是政商圈的“润滑剂”,都反映了他与高官商人的密切关系。
老大的“组织”不仅限于国内,还通过雇佣兵培训(我遇到的伊拉克雇佣兵白晓保)参与国际安保市场,涉及“一带一路”沿线的项目保护。他的顺义学院不仅是培训基地,还为海外任务输送人才。
老大并非单纯的冷血掮客。他说“有人想拿我开刀”,他退役时背负冤屈,或许曾因军功自视甚高,却被权力斗争牺牲。
这让他对体制既忠诚又戒备,决心打造自己的帝国。他对我的“欣赏,可能因为我让他看到年轻时的自己,但我的背叛也让他感到威胁。
老大掐灭烟头,语气冰冷:“你有两条路,一条是跟我走,去俄罗斯,帮我盯着那边的生意;另一条,你知道后果。”
我盯着他,脑海里闪过深圳别墅的奢华、南京工地的愤怒,以及老家饭馆里母亲的白发。我问:“俄罗斯那边的生意,是不是跟洗钱有关?还是别的什么?”老大眯起眼,笑了:“你真不该问这个。”
他挥手,老陈上前,给我看了一份文件,上面的人,已经批了几个大项目,涉及中俄边境的能源和军工。你要是不配合,连你家那小饭馆都保不住。”
那一刻,我明白了,老大不是一个人,他身后的网,深到连他自己都只是其中一环。
我想起U盘里的录音,里面有他在深圳别墅与一位高官的对话,提到“边境线上的货”和“北边的朋友”。如果我把这交给警方,也许能扳倒他,但也可能毁了自己和家人。
我假意答应,争取时间脱身。那夜,我趁看守换岗,偷了老陈的车,逃出学院,连夜赶往南京,找到那位记者朋友。我把U盘交给他,叮嘱他匿名投给中纪委,同时自己买了一张去南方的火车票,准备彻底消失。
24年冬,新闻报道了一起跨国洗钱案,涉及中俄边境的能源交易,数名高官落马,但老大的名字依然没出现。我躲在云南边境的小镇,开了一家无名小店,时刻提防有人找上门。
偶尔,我会收到匿名短信,内容只有四个字:“老大看着你。”
老大的背景让我意识到,他不仅是退役少将,更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在权力、财富和风险的夹缝中,他建了个隐形帝国,却也让自己成了棋盘上的卒。
他的军旅生涯赋予了他资源和野心,但也让他背负了无法洗白的阴影。我的选择,捅破了他的网,却也让我永远活在阴影里。
小镇的清晨被雾气笼罩,我站在无名小店的门口,端着一碗米线,目光扫过街角。半个月前,我把U盘交给南京的记者朋友,里面有老大在深圳别墅的录音,提到“北边的朋友”和“边境线上的货”。新闻爆出中俄边境的洗钱案后,我以为老大会被牵连,但他的名字从未出现。
我知道,他太狡猾,早就把自己藏在迷雾里。昨天,店里来了个操外国口音的顾客,点了一杯咖啡,临走时留下一张纸条:“张鹏让你别乱跑。”
纸条上的字迹歪歪扭扭,像临时写的。我烧了纸条,背上行囊,准备换个地方藏身。U盘的备份还在我身上,那是唯一的护身符,也是最大的危险。
老大的国际联系,是我在顺义学院和深圳别墅时零星听来的片段。伊拉克雇佣兵白晓保曾提到“中东的单子”,深圳别墅的会客厅里,偶尔会出现操英语的西装男,谈及“海外账户”和“能源项目”。
我一直以为这些是老大的生意经,直到南京项目的账目让我意识到,他可能在玩一场更大的游戏——一场跨越国界的权力与金钱交易。
那是个闷热的夜晚,别墅负一楼的会客厅灯火通明,我端着刚做好的川味水煮鱼,推门进去。
老大坐在主位,身旁是个金发碧眼的外国人,穿着剪裁得体的西装,旁边放着一个黑色公文包。桌上摆着几瓶飞天茅台,还有一摞文件,封皮上写着“Blackstone Energy Partners”。
我低头摆菜,耳朵却竖得老高。“张先生,”金发男用流利的中文说,“中东的油田项目需要你们的人手,安全保障得跟上。资金已经到位,迪拜的账户随时可以走。”
老大点了一支烟,淡淡道:“人没问题,学院那边刚训出一批,俄语、阿拉伯语都会。但你得保证,北边的线不能断。”金发男笑了笑,压低声音:“黑石集团从不失手。莫斯科那边已经点头,货走海参崴,干净得很。”
我退出房间,心跳如鼓。海参崴?中东油田?这些词在我脑子里炸开。
我想起顺义學院的白晓保,他教我健身时无意中透露的: 好的,我明白。
老大的国际联系远比我想象的复杂。他退役少将的身份只是起点,真正的帝国是他退役后用军方人脉和资源搭建的跨国网络。
顺义学院不仅是国内安保人员的培训基地,还为海外任务输送精锐,涉及中东、非洲和俄罗斯的敏感项目。
他的“华安国际”公司,表面上是安保服务商,实则是国际交易的掩护,核心业务包括:
中东安保业务,通过与黑石集团的合作,老大为中东油田和基建项目提供武装护卫。这些项目多与“一带一路”倡议相关,涉及沙特、阿联酋等国的能源开发。白晓保曾透露,他在伊拉克护送过油气管道的运输车队,任务由华安国际承接,背后有老大的影子。
老大的网络延伸到俄罗斯远东地区,涉及能源贸易和军工物资的“灰色运输”。录音中提到的“边境线上的货”,通过海参崴港走私的电子元件或稀有金属,绕过西方制裁,用于中俄的军工合作。这些交易通过离岸公司洗钱,资金流向迪拜或新加坡的账户。
顺义学院培训的雇佣兵不仅服务于国内客户,还被派往非洲和中东,参与矿产资源保护或冲突地区的“特殊任务”。这些人员多是退役特种兵,精通多国语言,纪律严明,忠诚于老大。
老大与黑石集团的合作,是通过华安国际的空壳公司在海外投资房地产或能源项目,清洗国内的灰色收入。他的别墅里堆满的茅台和古董,部分是海外客户送的“礼物”,如俄罗斯的伏特加和中东的黄金工艺品。
老大的国际联系并非一帆风顺。现实中,“一带一路”项目常面临地缘政治风险,如西方国家的反洗钱调查和俄罗斯内部的派系斗争。老大的生意需要在多方势力间平衡,既要讨好国内高层,又要应对国际监管,还要提防俄罗斯或中东合作伙伴的“背刺”。
25年春,我藏在云南小镇,却被老陈找到,押回北京顺义学院。我被捆绑在地下室的审讯室里,老大坐在我对面,身后站着两个陌生人,一个操俄语口音的中年男人,另一个是西装革履的华人,眼神阴冷。
老大扔出一份文件,封面上是“华安国际”的 logo,里面是中俄边境交易的流水记录,涉及一家注册在开曼群岛的公司。“你以为把U盘给记者就完了?”老大冷笑,“你动的,是北边的线。那边的人可没我这么好说话。”我愣住了。
录音里提到的“北边的朋友”,原来不是国内高官,而是俄罗斯的某个寡头,控制着海参崴的运输线。文件显示,华安国际通过黑石集团的迪拜账户,为俄罗斯采购了禁运的芯片,价值数亿美元。
老大的角色是中间人,拿了巨额佣金,但交易被西方情报机构盯上,美国的OFAC(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已经开始调查。
“你有两条路,”老大点了一支烟,语气平静,“一是去俄罗斯,帮我稳住那边的人,证明你的忠诚;二是留下,记者那点料,够你家破人亡。”我咽了口唾沫,脑子里乱成一团。去俄罗斯,等于跳进另一个火坑,可能卷入更危险的国际博弈;留下,我知道老大的手段,江西的小饭馆恐怕保不住。
更糟的是,U盘里的录音已经引发连锁反应,南京的记者朋友告诉我,中纪委和公安部联合调查,几个度假区高管供出了老大的名字,但证据不足,他依然逍遥法外。
两天后,我被带到北京郊区的一栋隐秘别墅。老大不在,但来了个新面孔——一个自称“詹姆斯”的英国人,操着一口流利中文。他自称是黑石集团的代表,实则是西方情报机构的线人。
他开门见山:“张的生意,踩了红线。OFAC查到迪拜账户的资金流,你手里的录音,是我们需要的最后一块拼图。”詹姆斯递给我一张瑞士银行的卡,里面有500万美金,条件是交出U盘,并作为证人出庭,指控老大的洗钱网络。
我盯着那张卡,心跳加速。500万,够我下半辈子衣食无忧,但也意味着彻底背叛老大,背叛那个曾让我敬畏的“帝国”。我问:“如果我拒绝呢?”詹姆斯冷笑:“你以为张鹏护得了你?他自己都泥菩萨过江。俄罗斯那边已经有人想拿他开刀,换取跟西方的交易筹码。”
我脑子里闪过老大在深圳别墅的画面,他曾说:“这世上有些门,开了就关不上。”
现在,我站在那扇门前,进退两难。交出U盘,我可能被老大的网络追杀;拒绝,我可能被西方势力或俄罗斯的“朋友”盯上。更别提国内的反腐调查,随时可能把我当作替罪羊。
当晚,我被关在别墅的地下室,门外是老陈和几个雇佣兵。我趁夜深,用从顺义学院学的技巧,撬开一扇通风窗,逃了出去。
我连夜赶到昆明,找到一个老同学,借了他的身份证买了张飞往泰国曼谷的机票。在机场,我把U盘的备份上传到一个加密云盘,设置了定时发送给中纪委和国际刑警组织,如果我72小时内没取消,文件会自动公开。
在曼谷的廉价旅馆里,我收到一封匿名邮件,附件是一张照片:我母亲在江西小饭馆门口,被一个陌生人尾随。我心如刀绞,知道这是老大的警告。我拨通詹姆斯的电话,告诉他:“我给你U盘,但我要安全通道,送我去第三国。”詹姆斯答应了,但条件是我必须在国际法庭上作证,指控老大的洗钱网络。
几天后,我被秘密送往新西兰,住进一个偏僻小镇的保护屋。U盘里的录音成为国际刑警组织和OFAC的突破口,华安国际的迪拜账户被冻结,老大的几个海外合伙人被捕。
但老大依然像幽灵,销声匿迹,只留下一句通过老陈传来的话:“你跑得再远,也逃不出我的手。”
25年夏,我在新西兰的小镇上开了一家咖啡馆,化名生活,时刻提防有人敲门。新闻里,华安国际被查封,老大的名字终于出现在中纪委的通报中,但指控仅限于国内的腐败案,国际交易的部分被大事化小。
我知道,他可能通过俄罗斯或中东的关系,转移了资产,藏在某个无人知晓的角落。
老大的国际联系,是一张横跨中东、俄罗斯和西方资本的网,每一根线都沾着血与金。他的军方背景让他游刃有余,但也让他成为多方势力的靶子。
我的揭露,撕开了一个口子,却远不足以摧毁他的帝国。我每天打开电脑,检查那个加密云盘,提醒自己:真相有代价,但沉默的代价更大。
每天清晨,我在厨房里忙碌,切菜、炒菜、调汤,熟悉的油烟味让我感到踏实。餐馆不大,但生意还算稳定,街坊邻居喜欢来这里吃一碗热腾腾的杂酱面,夸我的手艺好。
每当听到这些,我都会心一笑,想起在深圳别墅里为高官大商做菜的日子。
那时的我,满心想着出人头地;如今的我,只想守住这一方小小的天地。
偶尔夜深人静,我会翻出手机,看看当年的照片:顺义学院的训练场,深圳别墅的茅台酒瓶,还有南京项目工地上的黄土。
我想起老大那张深不可测的脸,想起白晓保爽朗的笑声,想起徐峰冷嘲热讽的眼神。这些记忆像刀子一样锋利,却也让我更加珍惜现在的平静。
现实教会了我,天花板从来不是触手可及的梦想,而是无数欲望与阴谋交织的陷阱。我选择了平凡,选择了自由,也选择了与过去的自己和解。或许,这才是真正的救赎。
完!